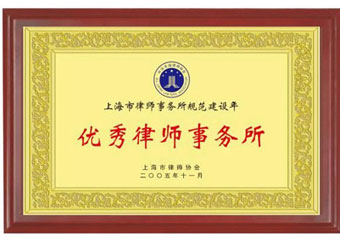謀殺罪的犯罪行為是由被告的行為或不行為造成的非法殺人。謀殺罪的犯罪動(dòng)機(jī)是蓄意或故意。什么構(gòu)成刑事犯罪的意圖一直是一個(gè)難以界定的概念。[2] 意圖可以分為兩個(gè)子類別:"直接意圖 "和 "間接/間接意圖"。大多數(shù)謀殺案涉及直接意圖,而且通常沒有問題,因?yàn)楸桓婷鞔_表示了他的意圖。[3]Woollin案涉及的是斜向意圖,正是這一案件類別出現(xiàn)了困難。為了更好地理解為什么Woollin案的方向可能缺乏明確性,有必要看看圍繞這一法律領(lǐng)域的問題,并確定一些以前有爭議的案件,然后調(diào)查是否應(yīng)該有一個(gè)關(guān)于意圖的法定定義。在間接故意的案件中,犯罪的后果不是當(dāng)事人的目的或目標(biāo),而是作為當(dāng)事人行為的副作用而發(fā)生的,他預(yù)見到了結(jié)果,但不一定希望如此[4];法官需要遵循司法指南,就這個(gè)關(guān)鍵術(shù)語的含義向陪審團(tuán)提供指導(dǎo)。在Woollin案之前,有一些謀殺案給司法部門帶來了問題,這些問題是由法官向陪審團(tuán)提供的關(guān)于間接意圖的指示引起的。[5]法院表示,有兩個(gè)問題需要考慮。
被告是否需要預(yù)見到這個(gè)結(jié)果?不良影響 "發(fā)生的可能性有多大,是必須幾乎肯定會(huì)發(fā)生,還是必須僅僅是可能發(fā)生?
第一個(gè)要研究的案例是DPP訴Smith案,在該案中,上議院裁定,如果一個(gè)人預(yù)見到其行為的自然和可能的后果,那么意圖就可以成立。這一判決被認(rèn)為是不正確的,1967年《刑事司法法》的通過推翻了這一決定。通過該法案,議會(huì)規(guī)定僅僅預(yù)見到死亡的可能性并不足以構(gòu)成意圖,并指出陪審團(tuán)沒有義務(wù)僅僅因?yàn)檫@是被告行為的自然和可能的結(jié)果就認(rèn)定被告是有意的;陪審團(tuán)要查看所有相關(guān)的證據(jù),然后對(duì)被告的意圖做出適當(dāng)?shù)耐茢唷7] 法院將此解釋為要求進(jìn)行主觀測(cè)試,這就解決了第一個(gè)問題的答案,但卻導(dǎo)致了對(duì)第二個(gè)問題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裁決。[8] 不良影響發(fā)生的可能性有多大,是必須幾乎肯定會(huì)發(fā)生,還是必須僅僅是可能發(fā)生?在Hyam案中,上議院認(rèn)為,如果一個(gè)結(jié)果是有意的,即使它可能不是被告所希望的,但如果它被預(yù)見到是一個(gè)可能的結(jié)果,那么犯罪意圖就成立了;[9]在這個(gè)關(guān)于意圖的含義的裁決中,不同的司法意見表明這個(gè)裁決是不令人滿意的,因?yàn)樗斐闪讼喈?dāng)大的混亂狀態(tài)。[10] 在Maloneey案中,對(duì)意圖的含義的處理方法被縮小了,法官們認(rèn)為,意圖不等同于預(yù)見,事件必須是被告行為的自然發(fā)生 [11] 。在Hancock & Shankland案中,法官們強(qiáng)調(diào) "道德上的確定性或壓倒性的可能性是構(gòu)成意圖的必要條件" [12] 。Maloney指示被批評(píng),因?yàn)樗鼪]有提供任何關(guān)于可能性的參考 [13] 。在Nedrick [14]案中,Lord Lane CJ解決了上述案例中意圖含義不統(tǒng)一的問題,他提供了一個(gè)被認(rèn)為是 "示范指示 "的內(nèi)容。

"如果指控是謀殺,而且在簡單的指示還不夠的少數(shù)情況下,應(yīng)該指示陪審團(tuán),他們無權(quán)推斷必要的意圖,除非他們確信,由于被告人的行為,死亡或嚴(yán)重的身體傷害是實(shí)際肯定的(除非有一些不可預(yù)見的干預(yù)),而且被告人明白這是事實(shí)"[15] 。
在試圖澄清關(guān)于間接意圖的法律時(shí),上議院在Woollin案中一致確認(rèn)了Nedrick的指示,并作了一項(xiàng)修正,同意了虛擬確定性測(cè)試的要求:將 "推斷 "一詞改為 "發(fā)現(xiàn)",以確保示范指示的清晰性。[16]上議院認(rèn)為,在涉及間接故意的案件中,除非死亡或嚴(yán)重的身體傷害是被告人被禁止行為的實(shí)際確定結(jié)果,并且被告人已經(jīng)意識(shí)到這一點(diǎn),否則陪審團(tuán)不得認(rèn)定為謀殺罪的故意。[17] 一些法律評(píng)論家對(duì)Woollin的指示表示歡迎,Smith教授將該判決描述為"重要的和最受歡迎的是,它在意圖和魯莽之間劃出了一條堅(jiān)定的界線......并應(yīng)結(jié)束實(shí)質(zhì)性風(fēng)險(xiǎn)指示" [18] 。
在他的評(píng)論中,Smith教授還指出并同意Hope勛爵和Steyn勛爵的觀點(diǎn),即對(duì)使用'發(fā)現(xiàn)'一詞的修改將會(huì)并應(yīng)該擺脫從一種心態(tài)推斷出另一種心態(tài)的奇怪和備受批評(píng)的概念。[19]Alan Norrie最初同意,該判決似乎結(jié)束了有關(guān)間接[間接]意圖的長期傳奇,但他表示,Woollin案可能不是這個(gè) "意圖 "領(lǐng)域的最后定論,因?yàn)橐赱間接]意圖的法律中取得一個(gè)結(jié)論性的立場并非不可能[20],"Woollin案沒有回答...判斷某人是兇手的道德依據(jù)"。[21] Arfan Khan指出,當(dāng)法官指示陪審團(tuán) "推斷必要的意圖 "時(shí),這實(shí)際上增加了控方證據(jù)的分量;這似乎違背了《歐洲人權(quán)公約》第6.2條。[22] 由于Woollin案的上議院同意Nedrick案的判決,因此出現(xiàn)了Woollin案方向不明確的問題。然而,Hyam案與Nedrick案相似,但結(jié)果不同,也沒有被上議院推翻。盡管如前所述,這兩個(gè)案件是相似的,但Hyam案的判決側(cè)重于基于預(yù)見的可能性,而Nedrick案的判決是基于虛擬的確定性和實(shí)現(xiàn)性的測(cè)試。有人認(rèn)為,上級(jí)法院制定的關(guān)于意圖的準(zhǔn)則并不明確,在審判法官指導(dǎo)陪審團(tuán)時(shí)可能會(huì)導(dǎo)致混亂。[23] Alan Norrie談到了這個(gè)問題。
"......眾議院在Woollin案中的觀點(diǎn)偏離了以前不愿意承認(rèn)Hyam不能與后來的案件站在一起的觀點(diǎn)。法官們此前一直 "不必要地......和危險(xiǎn)地......靦腆地宣布他們的兄弟或前輩搞錯(cuò)了"[25]......如果Hyam與Nedrick在實(shí)質(zhì)上是一樣的,那么Hyam夫人就不應(yīng)該被判定為謀殺罪并被駁回上訴......然而很明顯,靦腆會(huì)滋生法律的不明確性[26]。如果上議院不準(zhǔn)備糾正以前模棱兩可的決定,那么這將導(dǎo)致不確定性。很明顯,Woollin指令告訴我們,被告在以下情況下具有必要的心理狀態(tài):(1)行為的目的是殺人或造成嚴(yán)重的身體傷害;或(2)行為時(shí)正確預(yù)見其行為幾乎肯定會(huì)導(dǎo)致死亡或嚴(yán)重的身體傷害。但它并沒有如此明確地告訴我們這兩個(gè)方面的關(guān)系,而且方向也沒有對(duì)意圖和魯莽進(jìn)行明確區(qū)分。[27]沒有明確的界限,很難確定從一個(gè)預(yù)見的 "幾乎肯定 "的后果到一個(gè)預(yù)見的 "極有可能 "的后果,這將是意圖的證據(jù)。這些都很難區(qū)分,但這是謀殺和過失殺人之間的分界線'[28] 。陪審團(tuán)必須在考慮到所有證據(jù)和主審法官的指示后,確定被告是否有意殺人或造成嚴(yán)重的身體傷害。[29]法官關(guān)于意圖指示的司法指南被認(rèn)為是不令人滿意的,[30]有人呼吁在法規(guī)中規(guī)定該定義。
在討論是否需要一個(gè)立法定義來確保司法道德主義沒有進(jìn)入法庭的空間時(shí),我們必須記住,普通法的傳統(tǒng)態(tài)度是,犯罪本質(zhì)上是值得懲罰的不道德行為。正統(tǒng)的主觀主義在刑法中的主導(dǎo)方法是,當(dāng)違反法律時(shí),犯罪者應(yīng)受到懲罰,刑事定罪表達(dá)了社會(huì)對(duì)有責(zé)性的判斷。[31] 情緒在刑法中無處不在,就像在生活中一樣;當(dāng)激情和憤怒等情緒急劇改變一個(gè)人的行為時(shí),法律是否應(yīng)該更加同情?[32] 隨著社會(huì)和政府的道德價(jià)值觀的變化,法律也應(yīng)如此。[33] 司法機(jī)構(gòu)受到道德標(biāo)準(zhǔn)的影響,不可能阻止道德進(jìn)入司法程序 [34] 。刑法涉及一個(gè)道德判斷的過程。[35]法官和陪審員都有各自的道德和信仰,然而,法官應(yīng)該能夠?qū)⒆约旱牡赖缕姺旁谝贿叄⑾蚺銓張F(tuán)提出明確的無偏見的建議。Woollin指令并沒有告訴陪審團(tuán)在考慮意圖時(shí)要考慮哪些因素。陪審團(tuán)在決定一種心理狀態(tài)是否 "壞到 "可以被稱為意圖時(shí),可以使用他們的常識(shí)。然而,陪審團(tuán)是由12個(gè)隨機(jī)的人組成的,他們可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道德觀,對(duì)一個(gè)人來說可能是常識(shí)和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東西,對(duì)另一個(gè)人來說可能就不一樣了。對(duì)一個(gè)人的行為的道德評(píng)價(jià)涉及到意圖,盡管是無辜的行為,但由于這個(gè)人的動(dòng)機(jī),可能是不道德的。由于沃林方向的性質(zhì)和靈活性,不同的陪審團(tuán)對(duì)同一組事實(shí)可能得出不同的結(jié)論。
當(dāng)?shù)赖聠栴}出現(xiàn)時(shí),"判斷、指責(zé)和懲罰的現(xiàn)實(shí)產(chǎn)生了相反的壓力,保證了對(duì)無價(jià)值的法律科學(xué)的追求不可能成功" [36] 。安德魯-阿什沃思從威勒案[37]中發(fā)現(xiàn),陪審團(tuán)在審議案件時(shí)被允許有一些 "道德上的余地";[38]"如果法律太過超出他們對(duì)什么是合理的常識(shí)的概念,陪審團(tuán)偶爾會(huì)'反常'地拒絕定罪,[39]這本身就為法庭上的司法道德主義留下了空間。Smith教授[40]和Arfan Khan[41]主張將 "意圖 "的定義寫入法規(guī)。法律委員會(huì)的一份報(bào)告對(duì)這一問題進(jìn)行了調(diào)查,委員會(huì)的結(jié)論是[42]"現(xiàn)有的關(guān)于意圖的含義的法律應(yīng)該被編纂"[43];在他們的調(diào)查結(jié)果中,他們說簡單的定義應(yīng)該是 "為了帶來一個(gè)結(jié)果而行動(dòng)"。Ashworth指出,這是以Woollin方向?yàn)榛A(chǔ)的。[44] 該委員會(huì)還指出,對(duì)陪審團(tuán)的指示,即解釋與法律有關(guān)的事實(shí),應(yīng)以口頭和書面方式進(jìn)行。[45] 霍普勛爵在Woollin案中指出并指出:"我非常重視尋求一種既明確又簡單的指示。它應(yīng)該用盡可能少的字來表達(dá)"[46];這可以被看作是一個(gè)優(yōu)勢(shì),因?yàn)樯显V法院的批評(píng)之一是,主審法官在一夜休庭后完成了指示,可能使陪審團(tuán)感到困惑。[47]在Woollin案中,Steyn勛爵為初審法官制定了一個(gè)示范指示,以便在被告人意圖不明確的情況下使用,隨后在R.訴Matthews & Alleyne[2003][48]和R.訴Matthew Stringer[2008]案中使用了這一指示。
目前的定義在很大程度上是個(gè)案中司法法律制定的產(chǎn)物,法律委員會(huì)建議,如果將間接意圖的定義寫入法規(guī),那么將使用Woollin指令。意圖的定義似乎已經(jīng)達(dá)到了一個(gè)合理的穩(wěn)定狀態(tài),但由于法律的流動(dòng)性,不可能有完全的一致性,而且審判法官并不總是遵循示范性的指示。由于法院審理的謀殺案沒有一個(gè)是完全相同的,因此需要有靈活性,允許法官?zèng)Q定陪審團(tuán)應(yīng)該在哪些法律要點(diǎn)上得到指導(dǎo);正如前面所確定的那樣,意圖的定義仍然缺乏明確性,如果在法規(guī)中硬性規(guī)定該定義以給出明確的含義,法官仍然會(huì)保留很大的解釋權(quán)。
歷史上,法院對(duì)可接受性采取了嚴(yán)格的方法,據(jù)此,證據(jù)的排除不被認(rèn)為是一個(gè)問題,而獲得所述證據(jù)的方法基本上是不相關(guān)的。傳統(tǒng)上,根據(jù)英國普通法,人們一直認(rèn)為,只要證據(jù)與有關(guān)問題相關(guān),就可以被接受。這意味著,即使是被盜或通過非法搜查獲得的證據(jù)也被認(rèn)為是可接受的。1955年,戈達(dá)德勛爵拒絕了任何關(guān)于非法獲得的證據(jù)應(yīng)不予受理的爭論,聲稱 "法院不關(guān)心證據(jù)是如何獲得的"。這一理由一直保持到20世紀(jì)中期法院面對(duì)這一問題時(shí)。他們終于意識(shí)到有必要保持刑事程序的完整性,并軟化那些如果嚴(yán)格遵守可能會(huì)造成不公正的技術(shù)規(guī)則。在Kuruma v R和Noor Mohammed v The King這兩個(gè)相當(dāng)孤立的案件中,人們認(rèn)識(shí)到通過欺騙手段獲得的證據(jù)可以被排除,而是否接受類似事實(shí)的證據(jù)的問題 "應(yīng)該留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(quán)和公平感"。在上議院R訴Selvey一案中,這些權(quán)威被匯集在一起,在該案中,迪爾霍恩子爵著名地宣布,鑒于如此杰出的法官所說的話,除了 "這種自由裁量權(quán)的存在現(xiàn)在已經(jīng)明確確立 "之外,說什么都已經(jīng)太晚。正當(dāng)人們似乎正在采用一種更公平、更主觀的方法時(shí),這種進(jìn)步受到了相當(dāng)突出的打擊,1979年,上訴法院在R訴Sang一案中宣稱,根據(jù)以前的權(quán)威,他們沒有看到任何理由,可以以通過誘捕的欺騙性做法獲得的證據(jù)為由,排除證明性和相關(guān)證據(jù)。批評(píng)者對(duì)這一結(jié)果感到失望,強(qiáng)調(diào)有必要對(duì)這一原則的范圍進(jìn)行澄清。斯卡曼勛爵確實(shí)承認(rèn)了這一點(diǎn),但五次不同的、相當(dāng)混亂的發(fā)言提供了一個(gè)不那么令人滿意的答案。盡管他們沒有澄清,但他們承認(rèn),如果法官認(rèn)為證據(jù)引起的偏見超過了其證明價(jià)值,他總是有自由裁量權(quán)來排除證據(jù),但這純粹是附帶的。不幸的是,在提到基于任何其他理由的排除時(shí),他們的大法官說。
除了承認(rèn)和招供以及在犯罪后從被告人那里獲得的證據(jù)外,沒有自由裁量權(quán)可以拒絕接受相關(guān)的可接受的證據(jù),理由是它是通過不正當(dāng)或不公平的手段獲得的。上議院將關(guān)于可接受性的法律范圍的進(jìn)展引向了停頓。這一結(jié)果隨后被批評(píng)為缺乏明確性和限制性的先例。對(duì)立的公共政策爭論的不安導(dǎo)致了不久之后議會(huì)的反應(yīng)。他們認(rèn)為有必要進(jìn)行干預(yù),并制定一些準(zhǔn)則,以避免未來出現(xiàn)任何司法不公或混亂的情況。這一反應(yīng)就是1984年的《警察和刑事證據(jù)法》。自由裁量權(quán)是否過于開放,以至于無法發(fā)揮作用;以及它的目的是保護(hù)誰的利益?Ormerod認(rèn)為,應(yīng)該向法院提出一個(gè)更有條理的法定提議,而不是目標(biāo)如此寬泛,以至于讓法官 "從事虛假的平衡工作,這可能是無意義的"。他認(rèn)為,這需要對(duì)自由裁量權(quán)的目的進(jìn)行澄清和透明,法院可能會(huì)從更有條理的指導(dǎo)中受益。
第78條在 "公平 "的含義方面的模糊性,以及這種公平是針對(duì)誰的,是可以批評(píng)的。公平 "是一個(gè)相當(dāng)不明確的詞,司法機(jī)構(gòu)可以操縱它來表示他們喜歡的東西。僅僅這一點(diǎn)就可以保證是有問題的,因?yàn)橐粋€(gè)人對(duì)公平的看法在本質(zhì)上總是與另一個(gè)人不同的。此外,它是 "審判公平 "還是 "第六條公平"?
西蒙-布羅尼特承認(rèn),"由于法院對(duì)指稱的侵犯人權(quán)行為的重視程度極低,第78條的懲戒潛力被進(jìn)一步削弱。"在R v Khan (Sultan)一案中,法官們將相關(guān)性放在歐洲人權(quán)公約規(guī)定的一般 "原則 "上,并承認(rèn) "如果證據(jù)是在明顯違反第八條的情況下獲得的......這可能是與行使第78條權(quán)力有關(guān)的問題。這肯定會(huì)鼓勵(lì)人們相信,在有這樣的歐洲人權(quán)公約立法的情況下,人權(quán)會(huì)得到更好的保護(hù),但仔細(xì)觀察,沒有什么證據(jù)表明情況確實(shí)如此。當(dāng)對(duì)任何侵犯人權(quán)的行為給予重視時(shí),眾議院似乎首先考慮的是該權(quán)利在國內(nèi)法中的保護(hù)程度。
法官們?cè)谏鲜霭讣斜硎倦y以將歐洲法律適用于國內(nèi)法律。他們說,強(qiáng)加給英國法官這樣做的期望是'不恰當(dāng)?shù)?#39;,因此在以下情況下只能對(duì)這種違反行為給予有限的重視。警察的行為相當(dāng)于明顯違反了一些相關(guān)的法律或公約,根據(jù)常識(shí),這只是一種考慮,可以考慮其價(jià)值。然而,其重要性通常不取決于其明顯的非法性或不規(guī)則性,而是取決于其對(duì)訴訟程序的公平性或不公平性的整體影響。因此,正如Bronitt所認(rèn)為的,這種類型的違法行為只會(huì) "使天平傾斜",通過干涉隱私獲得的證據(jù)的可接受性不可能損害被告的第六條權(quán)利。然而,Teixeira de Castro訴葡萄牙案(1998年)是對(duì)這一理由的徹底挑戰(zhàn),在用盡英國法律的法律補(bǔ)救措施后,該案被提交給歐洲人權(quán)法院進(jìn)行裁決。隨后,新的標(biāo)準(zhǔn)被實(shí)施,其作用是將公平權(quán)擴(kuò)展到包括 "審前程序"。從那時(shí)起,法院將根據(jù)1998年《人權(quán)法》,參照歐洲人權(quán)法院的法律來解讀國內(nèi)法律。然而,這仍將繼續(xù)引起不一致,因?yàn)橐呀?jīng)確定 "公平 "是一個(gè)相當(dāng)不確定的概念。因此,堅(jiān)持'第78條的公平性'可以說意味著法院認(rèn)為這樣做就滿足了第6條的審判公平性,甚至沒有采用基于權(quán)利的排除法。
Hutton勛爵認(rèn)為,他 "沒有發(fā)現(xiàn)第6條的要求和英國法律(關(guān)于濫用程序)之間有任何明顯的區(qū)別,因?yàn)樗呀?jīng)在最近幾年發(fā)展。這一觀點(diǎn)得到了Simon McKay的進(jìn)一步支持,他將兩者之間的關(guān)系描述為'共生關(guān)系',認(rèn)為在最近的案例中,有證據(jù)表明公約對(duì)英國法律的影響,而且公約很容易適合民法和普通法體系。他說,"第78條可能會(huì)實(shí)現(xiàn)訴訟的公平性,但也可能不會(huì)。濫用程序理論的運(yùn)作更符合第6條權(quán)利和義務(wù)的觸覺性質(zhì)'。相對(duì)來說,可以說議會(huì)在第78條方面努力整頓一個(gè)不受歡迎的法律領(lǐng)域,所取得的成果確實(shí)比普通法已經(jīng)或?qū)⒁〉玫某晒嗟枚唷H欢覀儜?yīng)該承認(rèn),盡管這些條款很籠統(tǒng),但它們是一個(gè)很好的法定基礎(chǔ),隨著時(shí)間的推移、實(shí)踐和審前監(jiān)管的增加,特別是結(jié)合1998年歐洲人權(quán)公約的人權(quán)干預(yù),更有效的準(zhǔn)則將在此基礎(chǔ)上發(fā)展。探討《歐洲人權(quán)法案》頒布以來的發(fā)展,可以說明誘捕問題的解決程度(如果有的話)。
桑案之后和更健全的理論的逐步發(fā)展。
桑案無疑是當(dāng)時(shí)最突出的誘捕案。正如前面所討論的,早在1979年,它阻礙了可受理性法律的發(fā)展,就在它的發(fā)展勢(shì)頭上。其核心原則是 "誘捕 "在英國法律中不被認(rèn)可,獲取證據(jù)的方式不是法院要處理的問題,而且是完全不相關(guān)的。自該判決以來,本司法管轄區(qū)和其他司法管轄區(qū)一直在審查某些警務(wù)技術(shù)和欺騙性做法的可接受性。自1984年頒布《警察和刑事證據(jù)法》以來,法院更愿意考慮將誘捕作為排除證據(jù)的合理依據(jù),盡管有這種意愿,但他們并沒有輕易制定明確的規(guī)則,堅(jiān)持認(rèn)為 "每個(gè)案件都取決于其自身的事實(shí)"。該理論在接下來的15年或更長時(shí)間里發(fā)展成為現(xiàn)在被視為當(dāng)代里程碑式的R v Looseley; Attorney-General's Reference (no 3 of 2000)案件,這兩個(gè)案件的事實(shí)相似,在同一審判中被審理并作出相同的判決。這兩起案件的根本區(qū)別在于,在Looseley案中,被告只是被 "提供了一個(gè)犯罪的機(jī)會(huì)",而在后者中,被告被 "煽動(dòng) "或 "導(dǎo)致 "犯罪。在對(duì)這些案件以及這些短語進(jìn)行必要的探討之前,重要的是讓自己熟悉PACE之后出現(xiàn)的一系列判例法的事實(shí),Loonesley和總檢察長的參考是建立在這些事實(shí)之上的。
R訴Latif和Shazhad一案涉及兩名來自巴基斯坦的毒品販子。在一名為他們提供簽證的臥底海關(guān)官員的幫助下,他們開始向英國進(jìn)口價(jià)值320萬英鎊的海洛因。法院認(rèn)為,臥底官員沒有濫用程序,雖然認(rèn)為行動(dòng)不會(huì)以這樣的方式進(jìn)行,但法官認(rèn)為,被告沒有被誘使犯下他們本來不會(huì)犯下的罪行。他們的上訴被駁回。然而,在Teixeira de Castro訴葡萄牙一案中,便衣警察遇到了一位知名的毒品販子,詢問他的大麻。當(dāng)被告告訴他們,他無法滿足他們的需求時(shí),他們要求用大量的海洛因代替。被告讓他們與能夠幫助他們的人取得聯(lián)系。在見到他后,警察逮捕了他和被告。法院認(rèn)為,警察越過了誘捕的界限,因?yàn)槿绻麤]有他們的干預(yù),就不會(huì)發(fā)生這種特殊的犯罪,這被認(rèn)為是違反了第6條。
在Nottingham City Council v Amin一案中,一名出租車司機(jī)因在其執(zhí)照范圍外駕駛而被定罪,當(dāng)時(shí)他搭上了兩名臥底警察,他們以其他公眾成員的方式向他打招呼。法院認(rèn)為,由于沒有對(duì)被告施加壓力使其犯罪,因此接受警官的證據(jù)不會(huì)構(gòu)成偏見。與此類似,在R v Williams和O' Hare案中,被告因搶劫一輛被戰(zhàn)略性地放置并敞開的貨車而被定罪。法院認(rèn)為,該證據(jù)是可以接受的,而且警官的行為不構(gòu)成誘捕,理由是他們與罪犯沒有溝通,也沒有打算抓捕任何特定的盜賊。同樣,在R訴Smurthwaite和Gill一案中,法院認(rèn)為由臥底警察冒充合同殺手獲得的證據(jù)并不構(gòu)成誘捕,因?yàn)橛嘘P(guān)警察是被動(dòng)的,沒有煽動(dòng)犯罪。
考慮到這一點(diǎn),似乎普遍的共識(shí)是,如果法院發(fā)現(xiàn)被告被警察 "引誘"、"誘惑"、"造成"、"唆使 "或 "煽動(dòng)",那么這將導(dǎo)致訴訟程序的中止,以規(guī)避代表被告的程序性不公平或偏見的可能性。這個(gè)概念,雖然看起來很直接,但實(shí)際上遠(yuǎn)非如此。正如法官們所說,每個(gè)案件都取決于其自身的事實(shí),而關(guān)于被告是否被 "導(dǎo)致 "實(shí)施某一特定行為的問題將取決于一系列的因素。然而,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了一個(gè)一般的途徑,即法院在評(píng)估被告在多大程度上被 "導(dǎo)致 "犯罪時(shí),會(huì)在不同的案件中問自己同樣的問題。他們非常重視警察是否將一個(gè)機(jī)會(huì) "轉(zhuǎn)移 "到了一個(gè)通常不會(huì)有的環(huán)境中,或轉(zhuǎn)移到了一個(gè)通常不會(huì)有這種機(jī)會(huì)的人身上。下一章將努力深入探討法院為確保審判的公正性所做的復(fù)雜努力,以及他們?cè)谶@一過程中所考慮的因素。
第三章
在《盧斯利案》中確定,為了懲罰一個(gè)人而 "導(dǎo)致 "其犯罪,從根本上說是錯(cuò)誤的。這根本不是警察或司法機(jī)構(gòu)的職責(zé)。然而,同樣地,可以理解的是,警察為抓捕罪犯而實(shí)施的一些行為仍應(yīng)被接受。然而,問題的根源在于這種行為的可接受程度。潛在的問題是,法院在 "可接受的主動(dòng)警務(wù) "和 "利用人性的弱點(diǎn) "之間的界限在哪里,以及他們?nèi)绾蔚贸霰桓媸潜?"導(dǎo)致 "犯罪的結(jié)論?
機(jī)會(huì)的轉(zhuǎn)移
法院宣稱,僅僅向某人提供犯罪機(jī)會(huì)與向其提供通常情況下不會(huì)出現(xiàn)的特殊機(jī)會(huì)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(qū)別。尼科爾斯勛爵認(rèn)為,后者的不公正性是 "顯而易見的"。但是,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明顯的,他們做出這種斷言的理由是什么?這種區(qū)分是非常有問題的,而且具有非常主觀的性質(zhì)。
據(jù)了解,縱容這種不當(dāng)行為將破壞 "司法系統(tǒng)的尊嚴(yán)和完整性",并損害公眾對(duì)司法機(jī)構(gòu)的信心。
因此,目前的整體問題是關(guān)于警察的行動(dòng),以及他們的行為是否"......非常不妥,以至于使行政部門名譽(yù)掃地"。因此,問題似乎集中在警察身上。然而,這其中的困難在于,為了衡量警察的不當(dāng)行為的程度,法院在評(píng)估罪犯的罪責(zé)時(shí)似乎不得不偏離刑法的一般原則,而刑法的一般原則是取決于被告在犯罪時(shí)的犯罪意圖。通常不考慮被告的性格、背景或社會(huì)環(huán)境。然而,為了確定擺在他們面前的機(jī)會(huì)是否 "特殊",他們需要首先找到被視為 "非特殊 "的東西,反之亦然。為了得出這個(gè)結(jié)論,他們不得不評(píng)估被告的性格和社會(huì)環(huán)境,以及期望他心甘情愿地參與警察向他提出的犯罪活動(dòng)是多么合理。Squires指出,這與其他訴訟程序所采取的通常做法截然不同,他提出了一個(gè)例子,即被告被綁架并被帶入司法管轄區(qū)以避免引渡規(guī)則。這不需要考慮被告的罪責(zé)或特征等等。因此,誘騙與其他領(lǐng)域的法律有很大不同。為了弄清楚這一點(diǎn),有必要深入研究法院如何確定誘捕行為,以及在確定被告是否被 "誘捕 "之前需要滿足哪些基本要素和要求。Ashworth認(rèn)為,法院在確定誘捕時(shí)使用了相當(dāng) "不具體 "的方法。為了評(píng)估這一理論,有必要探討Looseley案中使用的方法以及其判決所依據(jù)的案例。很明顯,確定誘捕的主要標(biāo)準(zhǔn)有三到四個(gè),看似相似卻又不盡相同;如果沒有警察的參與,被告是否會(huì)犯下有關(guān)的罪行;被告是否被 "引誘"、"煽動(dòng) "去犯罪;以及被告被認(rèn)為是 "罪犯 "還是 "無知者"?如果這些問題中的任何一個(gè)可以得到肯定的回答,那么謹(jǐn)慎的做法是說被告沒有被'誘騙'。 深圳律師事務(wù)所
| 寶安南路律師談?wù)撡u淫,打人和艾滋 | 寶安南路律師談?wù)撘鈭D的定義案例 |
| 寶安南路律師解答有關(guān)不作為和親 | 寶安南路律師談?dòng)鴱?qiáng)奸法的概述 |